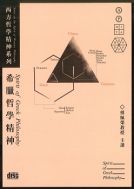專欄文章 Back

道家的永恆價值
傅佩榮教授
2012-09-20 道家以老子與莊子為其代表,有時也加上列子。列子的年代可能早於莊子,但是著作散佚,到了西晉的張湛為其作注,再傳於後世。然而,目前所見的《列子》已受魏晉玄學的影響,甚至夾雜了佛教故事。至於思想主旨則是:人生苦短,死後萬事皆休,一切皆為氣化,不如及時行樂。這種悲觀厭世之情,顯然有違道家意旨,不必在此深究。
老子有「小國寡民」的觀念,莊子也嚮往「上如標枝,民如野鹿」(君主有如高處的樹枝,人民有如自在的野鹿。)(〈天地〉),亦即都有「無為而治」的理想。這種理想在漢代初期形成「黃老治術」,與民休養生息。然而,一旦形成治術,落實為「用」,則其原始理想難免打了折扣。道家固然是如此,儒家呢?從漢武帝「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」以來,情況也好不了多少。如果即體言用,注定將會變質走樣,那麼在未能明體就想致用時,後果不是更加不堪設想了嗎?於今之計,我們只能盡力準確把握道家的思想,至於能否應用於生活中,則要看個人的造化了。
今日處於「後現代社會」,對於傳統基於理性所建構的價值觀(如仁義、禮樂),全都加以質疑,形成「價值歸零」的現象。譬如,近十餘年來蔚為流行口語的「只要我喜歡,有什麼不可以?」就是鮮明的例證。在古代,遭逢天下大亂,個人在社會上懷才不遇,所以一方面明哲保身,同時也培養悟道的智慧,冀求精神上的逍遙無待。在今日,則有民主制度保障人權,自由輻度少有拘限,資訊設備又提供了無比開闊的虛擬世界。這真是個「海?憑魚躍,天空任鳥飛」的美麗新世界啊!然而,越是多樣的選項,也將使選擇越加困難。自由一變而為壓力,因為在未能了解「自我」之前,「自由」往往只是任性盲動或恣意盲從的代名詞,其後果常為懊惱與悔恨,最後淪於「重複而乏味」的不堪之境。
有一弊,也可能有一利。道家批判社會上的既成規範時,也說過「絕聖棄智,絕仁棄義」之類偏激的話,聽起來有些後現代的意味。但是,這種「破」是建立在「讓生命在道中安頓」的智慧上的;破小所以立大,要讓自我回溯於一個完整而永恆的根源。任性不是自由,盲從更不是自由,只有回歸於整體的道中,化解了身心的執著,開啟了靈性的力量,以此為自我的真正主體,做到「外化而內不化」,然後才有自由可言。換言之,今日社會的外在自由,正是我們尋求內在自由的最佳契機。後現代社會所能提供的唯一優勢,正是道家思想可以大顯身手的新天地。
如果從哲學角度評估道家的得失,則正面的肯定是不言可喻的。西方學者習於以儒家為「倫理學」的宣講者,我們的辯護是「儒家不僅只有倫理學的成分」;但是要揭示儒家的形上學內含,總是難免多費唇舌而未必有效。至於道家,則自從老子說出了「道可道,非常道」一語之後,學者無不肯定「道」為形上學所欲彰顯之本體,因而也對道家另眼相看,視之為極富智慧的哲學立場。
西方哲人觀察萬物,見其流變生滅,不免提出深刻的質疑:「為何是『有』而非『無』?」萬物依其本質,皆為有始有終,在始之前及在終之後,本無一物,因此「無」才是萬物的真相。現在居然是「有」,著實讓人驚訝,而哲學即是「起源於驚訝」,進而探究其真相的一門學問。那麼,聽聽莊子怎麼說,他說:「古之人,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?有以為未始有物者,至矣,盡矣,不可以加矣。」(〈齊物論〉)意思是:古代的人,他們的知識抵達頂點了。抵達什麼樣的頂點呢?有些人認為根本不曾有萬物存在,這是到了頂點,到了盡頭,無法增加一分了。換言之,「未始有物」正是「無」的境界。這個無並非虛無,而是萬物的起源與歸宿,亦即是道。能夠悟道,即是解脫桎梏,隨物而化,孕生無窮無盡的美感。莊子說: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」(〈知北遊〉)意在斯乎!
※請尊重著作權,文章版權所有,但歡迎分享連結原址。未經清涼音及作者之同意,請勿轉載或轉寄。